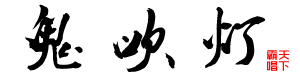难怪我总感觉马海波这个人平日里总是大大咧咧,今天却含糊得很,原来是因为这事儿。
不过说来也是,一般情况下这种忙我是毫不犹豫就答应的,然而偏偏现在不是时机:我奶奶明天下葬出殡,我虽然不是长房长孙,不用端灵牌领路,但是今天夜里我是要跪着守灵的,明天早上去出殡下葬,扛棺材的那几个人里面,我也是要算一个的——这是规矩,不能不遵守。你不做,无论你混得有多好,就算你当了县太爷,都会被别人戳后脊梁骨,骂你不孝,什么难听的话都会传出来。
我说过,在我们那里,世界太小了,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说得让人头疼。
我倒不打紧,左耳进右耳出,如清风一阵过。但是我父母却常年在这十里八乡地来往,我这个当儿子的,可不能让他二位老人家受这气。我爸倒也还好说,一辈子都是个老实巴交的汉子,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(此处绝无对他老人家不敬之意),拙于表达,也不擅沟通;我妈却不行,她这当大姐的人,向来就要强,最受不了别人的闲言碎语。
马海波和杨宇将这意思说完,都没有说话了,一脸期望地看着我。
我犹豫了一会儿,没吭声。
马海波和杨宇算是老油条了,也没有说话,倒是一个年轻小伙儿脸立刻就红了,着急得眼泪水涌了出来:“陆先生,你救救罗师傅啊……”——“先生”一词,在我们那儿的方言里并不是常用于,家里面向来是称兄道弟攀亲戚,实在不行就叫同志,这个词向来是对风水算命师傅的敬称。这个小伙儿我也见过,曾在色盖村碎尸案的专案组里面,还睡过一个房间。刑警队是老人带新人,看来这个是罗福安带的人,有感情,所以才会如此着急。
这个时候我大伯和小叔过来敬酒,见这气氛有些僵,问怎么回事?
马海波将情况讲给他俩听,大伯看着我,说听别人传你接了你外婆的班,却想不到你还有这本事,那去一趟呗,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,你奶奶要是地下有知,也会得意的。我小叔说这么多个堂兄弟姐妹,不差你这一个守灵的,放心,你奶奶最疼你了,不会怪罪你的。杨宇和几个警察也在旁边附和着,特别是那个年轻警察,眼眶都红了。我想了一下,现在晚上七点,如果来得及的话,我完全可以赶回来。
于是我起身前往灵棚,来到我奶奶的灵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头,然后与马海波等人离开。
借杨宇的车子因为要留下来接送亲戚,于是我把钥匙递给我小叔,乘坐着马海波这辆车子离开。路上的时候,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?马海波告诉我,吴刚手下那两个武警,一个是突发性肺炎,一个是落水死亡,而罗福安则是病毒性高烧,医院也检查不出个所以然来,本来今天中午就准备转院到市里面去的,但是听杨宇说你来了,便想让你来看看,毕竟你在这方面,是大师……
我说得了吧,咱们几个人,没必要这么肉麻吹捧。
杨宇在后面笑,说还真不是吹捧,我感觉你这个人有灵性,气场足得很。我昨天晚上做噩梦,又梦到我拉出了一坨全是黑色虫子的翔来,吓得一声冷汗醒了过来,结果你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坐在副驾驶室的我扭过头去含笑威胁:“看来你很怀念那种味道,要不要再试一试,当然,我的花样越来越多了……”
杨宇吓得又冒了一身汗,连连摆手:“不用了,不用了……”
我们哈哈大笑,车里面有着浓浓的情谊。
原本有可能成为敌人的一伙人,现如今都是亲密无间的朋友,这便是宽恕和圆滑的效果,比暴力更加有力量。当然,这些都是值得一交,而且足够聪明和醒目的人,对于某些浑不吝,你越退让,便越蹬鼻子上脸,欺压到你头上来。一个男人的成长,就在于审时度势,该恶的时候恶,该善的时候善,分清楚谁是你的对手,谁是你的朋友,这远远比财富要更加重要些。
所幸我渐渐地知道了这些,同时我也更加明白一个道理:争勇斗狠,就会四处树敌,无论你有多厉害,终归有比你厉害、比你狠毒的人出现。所以,养蛊人的“孤、贫、夭”三结局,其实也与这个有关。
然而,遇到这世间的不平事,就忍了、就让了、就无动于衷麻木了?当做看客旁观,是么!
每一个血液未冷的人都不会这么做。
我不是圣人。
当我开始渐渐地用另外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,我恐怖地发现:无论我们怎么挣扎,这天道都一直在我们的头顶上缓缓运转,从不偏移,命运的河流无论如何分叉汇合,最终会流入大海,不可逆转。
什么是大势?这便是大势!
即使你知道会这样,你看到了,但是仍然不可避免地随波逐流而去。
********
罗福安在县人民医院住院部的三楼病房,门口守着他婆娘和一个柔弱得像豆芽菜的少女。
我们到了病房的时候,已经是晚上九点钟,十月份有些秋凉,这娘俩挤在走廊的长椅上,看着有些瑟瑟发抖。马海波走过去抱着罗福安这个七八岁大的女儿,问丫丫,怎么都在外面等着啊,进去啊?丫丫摇了摇头,说里面好冷啊,不去。罗福安他婆娘在旁边解释,说刚才孩子闹太冷了,结果就跑出来了,本来打算去里面睡一觉的,结果这妮子死都不肯。
马海波笑了笑,说孩子嘛,总是不喜欢病房里面额消毒水味道,且由她吧。
我在看着这孩子一双恐惧的眼睛,发亮,有种不自然的飘忽。这个时候我的警觉性提升起来,将右手中指放到唇边,沾了一点口水,然后放在空中,汗毛有一种微凉的酥麻感;而当我的眼睛开始关注到病房里面的时候,一种阴森寒冷的诡异感觉,立刻从我心中浮现起来。
不对,这房间里面有古怪。
我伸手将后面的马海波几个拦住,快速念了一段“金刚萨埵法身咒”,然后双手在结着外狮子印,一步一步地走近病房门口。不知道是马海波他们单位福利待遇好,还是罗福安的病情比较特殊,反正这是一间单人病房。透过门上的玻璃,我可以看见一个胖子正躺在床上眯眼睡觉,因为怕打扰他的睡眠,所以关着灯,黑黑的,然而我透过窗外微弱的视线,却能够看见。
在模糊的视线中,我看到一个古怪的东西正浮在罗福安的头上。
这景象只有通过朵朵赋予我的鬼眼,方能够看清。
这是一个如同悬浮水母一般的东西,柔软如同水中头发一般的身体在罗福安的头上逗留着,没有颜色,因为一般人是看不到的,但是因为它的存在,所有的光线都不能够融入那一团区域,所以显得格外的暗。
这暗,便在视觉上形成了黑影。
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鬼玩意,却能够看到有淡淡的能量流动,从罗福安的身体中被吸取出来。
这种能量流动其实我还是熟悉的,一年以前,我曾经在每个星期六的下午,带着朵朵蹲守在东官各大医院的停尸房附近,就是吸收这种东西。它的名字叫做天魂,古称“胎光”,也有叫做主魂、元神的,是人从胚胎娘肚子里面带来的先天一气,人死后,这天魂遵守能量守恒定律,天魂归天路,为良知,亦是不生不灭的“无极”,因有肉体的因果牵连,上升至空间天路的寄托处,暂为其主神收押。
此谓“天牢”也。
死人天魂无用,活人天魂被吸过多,则阳寿顿无,谈个毛的治病救人啊?我也管不得这鬼东西是什么玩意,右手已经揣入怀中拿震镜,左手打了手势,让身后的人全部往后推开。通过真言的力量,我已经将自己的信心攀升到了巅峰,深吸一口气,猛然将门锁拧开,几步踏到床前,高高扬起手中震镜,一声“无量天尊”喝出,顿时金光闪耀。
那团肉眼不能见的东西浑身一震,竟然浮现在了我的视线中。
我看到有粉红色犹如水母鱿鱼一般的生物在我眼前,浑身都是柔软的触手,密密麻麻地浮动着,最长的一只,竟然就直接黏在了罗福安的后脑勺上面。我趁着它稍一凝滞,双手便朝它抓去。这东西看似水母,果然滑溜无比,如同涂了一层润滑油一般,然而幸好我好久没有剪指甲了,留得一手好爪子,反手一扣,将其紧紧抓在手中。
于此同时,朵朵和金蚕蛊同时出现,金蚕蛊直奔这鬼水母连接罗福安的那根触角去,而朵朵则朝着那东西喷了一口寒气。
这寒气是朵朵炼化了魂玉中被蚩丽妹所收藏的部分精魄之后,根据《鬼道真解》中的法门,修炼成功的。
寒冰鬼火。
此火非明火,而是来自地狱中的幽火——地狱是什么,鬼才知道!当然,这是鬼道真解中所杜撰的,大家呵呵一笑吧。
被朵朵这一口寒气所喷到,这鬼水母顿时所有的触角都全部收了回来,瞬间变成了拳头大的一个红色肉团,然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,这东西竟然朝我直扑而来,如同一个包袱皮一般,将我笼罩住。
啊——
我顿时窒息了,如同淹没在水中。
下一篇: 第十六卷 第四章 问情
上一篇: 第十六卷 第二章 乡下酒席